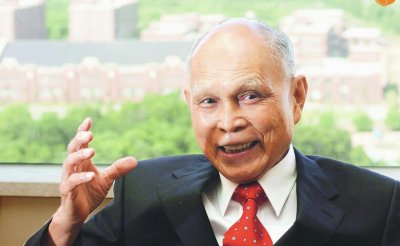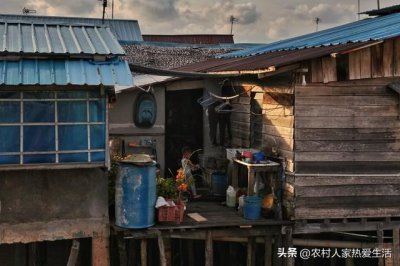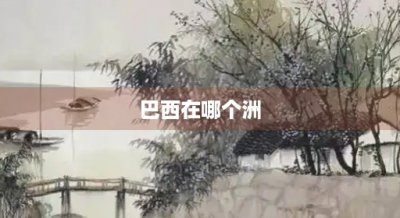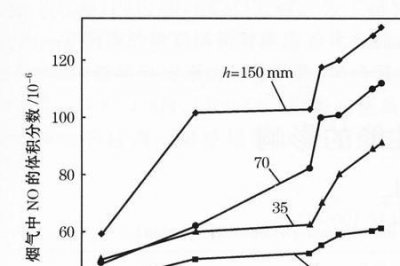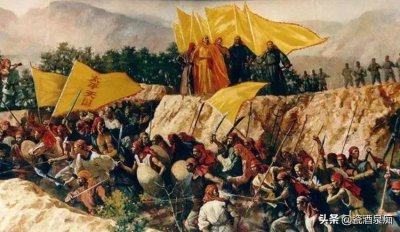费米悖论的文学解释
费米悖论的文学解释
让我们将费米悖论置于文学的透镜下,用隐喻与诗性解构这宇宙级的沉默之谜——
1. 《荒原图书馆》的悖论
宇宙若是一座无限延伸的图书馆(如博尔赫斯的巴别塔),
每本书都写着一种文明的可能。
我们翻开扉页,却发现所有文字都停留在空白章节——
书架间的回响只有自己的呼吸声。
是文明注定自我焚毁?
还是语言早已在熵增中褪色成密码?
这座图书馆或许从不渴望读者,
它只是用寂静拷问每一个闯入者:
“你为何执着于被看见?”
2. 《小王子》的星际孤独
想象所有星球都是玫瑰园,
每朵玫瑰都在用电磁波歌唱。
可当小王子穿越星系,
却发现所有花园早已枯萎——
刺的锋芒比花瓣更早抵达光年之外。
或许文明如玫瑰,
盛开即意味着凋零,
而宇宙的黑暗土壤里,
美与毁灭的根须始终缠绕。
3. 《奥德赛》的迷失航程
人类是向星海投掷木筏的原始部落,
用射电望远镜编织渔网,
打捞亿万年前的星光残骸。
但深渊始终以沉默回应呼喊,
像荷马史诗中独眼巨人的洞穴,
吞噬所有冒险者的回声。
这趟奥德赛没有塞壬与神谕,
只有航程本身在低语:
“迷途即是归途。”
4. 《楚门的世界》终极剧场
若宇宙是一出精心编排的戏剧,
人类是唯一被允许觉醒的角色。
其他文明皆是舞台背景的虚影,
导演用黑暗森林法则涂抹第四面墙。
我们触碰幕布的瞬间,
所有聚光灯骤然熄灭——
存在的意义,正在于识破这场孤独的共谋。
5. 《安徒生童话》的冰封寓言
外星文明或许是海底的人鱼,
将歌喉抵押给暗物质的海巫,
只为在超新星爆发的刹那跃出海面。
而人类举着望远镜跪坐冰原,
错把极光当作人鱼鳞片的反光。
童话的残酷在于:
追寻者与被追寻者,
永远困在时间流速不同的气泡里。
文学视角的终极叩问:
费米悖论像一面宇宙棱镜,折射的并非外星文明的存在与否,而是人类对自身意义的焦虑——
- 当我们在荒原点燃第一簇篝火,却无人应和时,这团火该为**照亮**还是为**取暖**而燃烧?
- 若所有史诗终将湮灭于热寂,此刻书写诗句的手,是否比诗句本身更接近永恒?
或许答案藏在那句古老的文学母题里:
“伟大的沉默不是拒绝回答,而是提问本身已然完整。”